亲子鉴定师:我拒绝了那个女人的作假要求
亲子鉴定师:我拒绝了那个女人的作假要求
作者 | 陆六六
ID |iiirenwu
作为一名职业鉴定人,在过去20年里,邓亚军借助DNA技术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进行亲子鉴定。
这当中,多数的鉴定结果可以顺利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
但仍有小部分“排除结论”会让故事走向“很遗憾,孩子并非你亲生”的无奈结局。
对于邓亚军来说,一纸报告写明的只是一个准确率无限接近100%的结论,可对于当事人来说,亲子鉴定的结果可以影响和决定很多:
一对夫妻的感情、一个家庭的未来,以及一个孩子的人生道路。
在所有邓亚军接手的委托中,有90%是男方主动提出的。
当亲子鉴定报告最后显示“不支持xx为xx的生物学父亲”时,绝大多数男人会选择离婚、分手,一段感情从此走向消亡。
于是多年来,许多媒体以“婚姻粉碎机”来形容邓亚军的工作,对此她很是反感:
“我真的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吗?还是这个家庭本来就有问题?”
在她看来,自己只是那个揭开真相的人。
“被欺骗的人有权知道真相。”

电话铃又一次响起,邓亚军知道来电人是阿红,接起,果不其然。
过去几天,女人已给邓亚军打了几通电话,每一次都情绪激动,时常话还没说几句就哽咽哭泣。
此前阿红带着儿子和婚外情人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阿红与情人的骨肉。
对于这样的结果邓亚军并不吃惊,甚至见怪不怪。
从业多年,她见过许多更离谱的事:
祖孙三代一同鉴定,最终发现孙子其实是爷爷与儿媳妇生的孩子;
一家四口判定血亲,结果证实外孙竟是外公与自家闺女所生的孩子;
双胞胎姐妹的生父不是同一人,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母亲两天内跟情人、丈夫分别同房,结果恰巧同时受孕......
“乱伦又颠覆”,尽管故事已足够让人“三观尽毁”,可讲述者邓亚军的语气始终平和。
“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看真相”,情绪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那一天邓亚军将结果告诉阿红后,女人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她告诉邓亚军,自己与丈夫结婚多年,感情一直不错,婚外情是因为一时冲动,所以发现怀孕时,她也不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
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长相却越来越不像老公,阿红怕事情败露,便带着情人和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果不其然,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鉴定结果出来后,阿红不断拨打邓亚军的电话,声泪俱下地央求她制作一份假的报告,“钱不是问题”,只要能骗过丈夫,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没有犹豫,邓亚军一口回绝了阿红的请求。
一方面是技术原因:
“亲子鉴定要求数据和峰图必须一一对应,这些都是自动化鉴定仪器做出来的,别人想做假根本不可能”;
另一方面则源于邓亚军本人的想法——
报告作假是严重违背行业职业道德的行为,“这绝对不可能”。

邓亚军(右)
邓亚军的倔强和坚持早有体现。
1996年,24岁的邓亚军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的本科学业,随后便在当地警局成为了一名法医。

邓亚军本科毕业照
在邓亚军的描述里,自己上班的单位周围有成片的玉米地,平日见不到什么人,是常见的“抛尸现场”。
差不多隔几天就会有农民跑到警局报案,说自家农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彼时邓亚军是警局里唯一一位女法医,“什么案子她都去,只要听见需要现场法医,她拎着工具箱就往案发现场跑”。
即使很多年过去了,同事对邓亚军最深的印象仍是如此。

做法医时期的邓亚军(中间,白衣服)
上世纪90年代,社会正处于机遇与动荡共存的时候。
作为一线警务人员,邓亚军经常需要面对大案、要案。
抢劫杀人、虐杀碎尸,她看到过许多血腥凶残的现场,“半夜接到通知是常有的事儿”,为了方便工作,她时常选择睡在单位。
当时警局还有一位男法医,第一次在现场看见呈现“巨人观”的尸体就吐了一地,最后还是由邓亚军完成了解剖工作。
邓亚军成为法医时,中国刚开始尝试将DNA检测技术运用于刑事侦查活动,由于种种限制,该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成熟。
1991年,河南省焦作市的一位农民报案,声称自己的妻儿已失踪多日。
此后,公安机关展开寻找、侦查,最终在某机井旁的水塘里打捞出了二人的尸体。
法医证实女死者生前曾遭受性侵,并在其体内成功提取到了凶嫌的DNA样本。
但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该样本只能确定凶手是一个O型血的男人。
因为线索太少且证据链不够完整,该案始终悬而未决。
直到2016年,我国建立并进一步完善DNA数据库,当年的办案民警才在其中寻得线索、找到真凶,而彼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刚入行的邓亚军
同样的无奈也体现在邓亚军的工作里——
在DNA技术尚不成熟的当年,很多高度腐败的尸体很难判断具体身份。
尸源无法确定,大量命案侦破工作走入“死胡同”,几乎年年都有无头公案。
如何才能打破僵局?邓亚军想了很久。

在一线当了3年法医后,邓亚军考取了母校的研究生,继续攻读法医学。
2000年夏天,邓亚军又在同学的建议下进入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初次尝试接触了DNA理论研究。
那时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实际应用中,DNA技术都是一个极为新鲜的“舶来品”。
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未来和走向,就连邓亚军自己在最初,也只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课题活动”,一切都是碰巧,一切又好似冥冥中注定。
这之后2年,邓亚军获得了博士录取资格并辞去了法医的工作。
“我仔细想了一下,念完博士应该也不会回到那里了,因为我已经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她决定不给自己留后路了。
“其实我是法医的叛徒。”

邓亚军做法医时期的现场图片
29岁那年,邓亚军瞒着所有人辞了职,交出警衔那天她想起了大哥邓治国——
作为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大哥一直是她的“偶像”。
在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时,她第一时间拨通了大哥的电话:“我只和他说了一句话,‘邓治国不好意思,我现在是博士了’。”
邓亚军念博士的第一年,国内非典疫情暴发。
在完成第一批ELISA试剂盒(一种抗原抗体试剂盒,可以帮助医生非常有效地在疑似病例中甄别出“非典”病人)的研制工作后。
为了进一步了解与攻克病毒,“华大”准备培养更多的SARS病毒,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指令下达后,一位病毒专业的博士当天便提出了辞职,另一位数据专家也在留下一封告别邮件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眼见着培养病毒一事无法推动,邓亚军和另一位同事主动站了出来。
在三次前往疫情重灾区采集“非典”病人血样后,她们走进了实验室。
而在此之前,二人对病毒学的了解,甚至都达不到“入门”级别,“没有任何想法,因为那种形势也顾不上多想”。
有些事是一定要完成的。

邓亚军(右)进实验室前
根据生物安全防护规定,培养“非典”病毒的工作,需要全程在P3实验室内完成。
而这也就意味着,她与另一位同事,需要穿着三层防护服,在完全密封且负压的室内工作。
(国际上根据实验室的密封程度,将实验室分为BSL-1到BSL-4,p4实验室为全球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实验室。)
在这之前,科研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工作的时长最多为8小时,而邓亚军与同事则达到了“平均每天12个小时”。
“内分泌严重失调,满脸都在冒痘,碰上生理期我和另一个女同事进去,出来就没例假了”。
“可能学法医的都不怕死吧”,即使过去了很多年,讲起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候,她的语气里仍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可能也是无知者无畏”。


“非典”疫情过后,邓亚军正式踏入DNA亲子鉴定技术领域,谈起这项她极为向往与热爱的研究事业,她坦言DNA检测技术已经被误解很久了。
时至今日讲起DNA鉴定,外界的第一反应仍是那些八卦的“狗血剧情”。
加之各类影视作品不遗余力地渲染与描述,仿佛该项技术存在的意义,就只为了服务婚姻中的危险关系。
“其实不是的”,邓亚军从来不这样认为,“DNA最大的一个运用,是在大型灾难中识别遇难者身份,比如空难、地震、海啸等。”
成熟且专业的DNA检测技术不仅能推测出个体的性别、人种、肤色,甚至还能预测出瞳孔与头发的颜色,和部分相对显著的面部特征。
例如,2004年,国外某地发生了一系列杀人案件,现场目击证人声称嫌疑人是一名白人男子。
此后警方以此为方向展开侦查却始终无果,直到法医从现场提取的DNA断定嫌疑人理应是名黑人男子,案件才得以水落石出。
“进行个体识别只有DNA鉴定是最准确可靠的”,换言之: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面前,DNA鉴定技术极有可能是亡灵“魂归故里”的唯一方式。

邓亚军参加节目(中间,黑色衣服)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矩震级9.3的海底地震,进而引发了“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
印度洋大海啸。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邓亚军在电视上看见“灾难已造成上万人死亡。
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

某国印度洋海啸前后卫星图对比
当天晚上,她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请,2天后就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回应:
海啸之后,泰国灾区留下了大量无法确认身份的遗体,而这其中大多数为前来度假的外国旅客,“那面(指泰国)的人说,非常需要中国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
得到回复的当天下午6点,邓亚军和其他4名同事就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办理了护照与签证紧急飞往泰国。
“回家就用了15分钟收拾行李,防护服、物证袋、采样工具什么都准备好了。结果因为太着急,所有吃的和洗漱用品全都忘了。”
正式出发前,副所长对即将出发的5人说: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 ,这种灾难现场可能会引发登格热、疟疾,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不会死人,还可以回国治,就怕霍乱,你们要是得了霍乱,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邓亚军和同事们在出发前就看见了“最坏的结果”。

邓亚军(右一)与同事前往泰国进行国际救援
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时,邓亚军刚刚32岁,而同她一起奔赴战场的伙伴,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
“出发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来,我还给几个好朋友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就是没敢告诉妈妈,当时真的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
12月31日,邓亚军一行人抵达泰国普吉岛,在经历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她们在受灾最严重的攀牙地区,看见了毕生难忘的画面:
“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铁;
有些地方堆着刚刚发现的尸体;当地的有些村民三五成群,继续寻找失踪的亲人和朋友。”
“在攀牙的两座寺庙里,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
在其中一座寺庙的左侧,就是一排排简易的棺材,触目惊心。
这是真正的现场,一排排高度腐败的尸体横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惨不忍睹。”

印度洋海啸现场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邓亚军一行人与国际DVI组织(多国救援人员组成的国际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展开了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过程中,邓亚军与同事首先要给每一具尸体编号、量尸长,之后再寻找与收集遇难者身上的项链、耳环、戒指、衣裤等遗物。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亲自做,每次一靠近尸体就会反胃,只能一次次强行将不适感压下去”。
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邓亚军形容当时的场景为:
“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你离那五百米,都闻到那股臭气。”

印度洋海啸现场
对于高度腐败的尸体,DNA检测几乎是对其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
在当时,泰国当地的所有实验室都不具备检测的条件和技术,如此,大量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
这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纠结中,邓亚军做出了决定:
“我让同事翻译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能做,所有费用我们承担。”

邓亚军在救援现场拍摄的图片
这之后不久,邓亚军一行人带着首批遇难者DNA样本回到中国,而后便是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
在此后近4个月的时间,她们借助技术帮助近2000位遇难者确认身份、找到家人。
此后根据计算,邓亚军团队对于骨骼疑难样本的检测成功率为84.7%,而彼时国际平均水平也不过50%。
后来,那些DNA数据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成为了两国友谊的特殊信物,当地DVI组织称:
“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做得太好了!”

邓亚军参加央视《面对面》专访
完成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工作后,邓亚军接受了央视《面对面》的采访。
观看样片时,她发现编导将那一期的节目取名为“代表中国”,“有些纠结和忐忑”的她找到节目组询问理由,编导说: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代表了中国。”

在邓亚军的职业生涯里,她几乎不曾感到“力所不及”。
科研工作固然艰难辛苦,可终归有规律和方法可循。
然而在踏足DNA亲子鉴定领域之后,她时常感到“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
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那些躲在数据之后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邓亚军接待的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来自一位怀孕2个月的女人。
对方告诉她,自己因为身体原因结婚10年不孕,不想和情人仅发生了几次关系便“有了”, “她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
由于孕早期的胎儿DNA样本极难提取,且存在影响胎儿正常发育的风险,所以邓亚军便建议女人再等等,可对方仍决定冒一次险。
此后邓亚军尝试了各种办法,始终也没能从女人的血液里成功提取出胎儿的DNA,鉴定无法正常进行。
这之后几天,女人再次找到邓亚军,并极为无奈地说,为了保住婚姻和家庭,她最终还是决定将孩子“拿掉了”。
她不确定自己此生是否还有成为母亲的机会,也不确定这段激情引发的婚外情日后会不会败露。
但在那个当下,女人很是确信,她真的很想与丈夫共度余生。
时至今日,邓亚军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女人,想她日后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面对朝夕相处的爱人,“所以说还能相信爱情吗?我其实更相信欲望”。

自2002年涉足亲子鉴定领域以来,邓亚军在鉴定所的接待室里,听过、见过几万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矛盾、纠结、疑惑、背叛、后悔、仇恨、惊讶......
复杂的情绪纠缠在复杂的故事里,最终组合出一组组带有基因“记忆”的DNA片段。
情绪可以隐藏,故事可以隐瞒,可DNA不会骗人,它就是个体的全貌,是人性和欲望的证明。
过去几年,邓亚军成立的鉴定中心平均每年要承接1万例亲子鉴定委托。
在这当中,“排除”亲生父子(女)结论大约占据10%~20%,也就是说,在这一万人中,最多有2000个人在为“别人养孩子”。

邓亚军:2万例中有20%的排除概率
在我国刚刚将原来主要由司法系统内部机构操作的DNA鉴定向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放开时,邓亚军说出的“大约20%的排除率”曾让许多人瞠目结舌。
有人借题发挥说她是利用个人隐私赚钱,是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粉碎机”。
争议最多的那些年,就连邓亚军身边的朋友都会半开玩笑地问她:“今年你又拆散了多少家庭?”。
刚入行时她也曾为此纠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不再想了。
邓亚军自己就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因为两个孩子长得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怀疑是不是医院搞错了”。
为此,她也曾替儿子和老公做过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兄弟二人是异卵双胞胎,也的的确确是她和老公的骨肉。
问题不是因为亲子鉴定产生的,问题本身就存在。

在所有找到邓亚军进行亲子鉴定的人中,男性占到了90%。
“他们一定是这当中的弱势群体,因为母亲一定知道孩子是谁的,但男人就不一定清楚了”。
多年前邓亚军曾接触过一位父亲,因为儿子长相过于清秀,和相貌平平的自己没有半点相似。
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都怀疑孩子并非亲生,为此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当邓亚军告知其亲子鉴定显示二人系亲生父子时,男人喜极而泣,“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说以后再也不用吃抗抑郁的药了”。
“人到中年,你别的都不用想,真的不用想太多,只要确定孩子是你的,老婆是你的,你就很幸福了。”

邓亚军:“我只相信鉴定结果”
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亲子鉴定在某些人眼中也成了女人是否出轨的检测工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邓亚军曾在一对老夫妻的委托下,替一个被引产的7个月大的死胎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确为儿媳与情人的骨肉。
拿到结果时,老夫妻在鉴定所内对儿媳破口大骂、拳打脚踢。
也是在此时邓亚军才得知,自成婚以来儿媳长期遭受婆家人的打压与言语侮辱,婆婆最常说起的一句话就是:
“女人不生孩子,那结婚干什么?”
可怜又可悲。
亲子鉴定可以判断血亲,却不能断定人性,“DNA技术的发明是为了判断强奸犯或者致孕者是谁”。
它从来不是审判女人的工具,它是为“真相”服务的技术——
之前邓亚军就曾为一名因公殉职的工人进行“遗腹子”鉴定,最终成功帮其遗孀争取到赔偿。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显示,近些年选择主动进行亲子鉴定的人正在逐渐增多。
于是一些有关“道德伦理的危机”的讨论也由此衍生,对此邓亚军始终持中立态度。
多年来,她见过,在发现养了16年的孩子并非亲生后,仍选择继续亲情的父亲;
也见过明明孩子是亲生,却依旧拒绝支付抚养费的父亲;
还有女人为办理领养手续,兴冲冲地抱着“老公捡来的孩子”鉴定,结果却发现孩子其实是丈夫的亲生孩子......
有亲情不一定是亲生,是亲生不一定存在亲情。
所以“亲子鉴定”真的和“道德危机”相关吗?任何人都给不出标准答案。
“作为一名鉴定人员,我不是伦理学家,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伦理问题,那需要人们自己去警惕和反省。”

现如今,邓亚军与同行们也将目光放到了“打拐寻亲”的公益事业上。
几年前一位寻子18年的父亲,拿着一份DNA样本找到了她,无比激动地说自己找到了丢失多年的孩子,请她进行一次亲子鉴定。
在后续的谈话中,那位父亲告诉邓亚军,自己的儿子是在医院离奇失踪的。
孩子丢失后,他的老婆因为过分自责,已经精神失常了,如今终于看见希望了。
DNA检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那位父亲便每日都到鉴定所从白天等到夜里。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两组样本不存在血亲关系——他找错人了。
“他的眼神一下就涣散了,整个人瞬间就颓了”。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邓亚军仍记得那位父亲在得知结果后失望的样子,“他愣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告诉我‘那就继续再找呗’。”
类似的故事太多,以至于邓亚军已习以为常。
这些年,她也会想起那些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和与他们相关的故事。
但想过之后呢?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因为真相就在那里。

邓亚军始终忘不了小禾。
差不多10年前,邓亚军受当地公安机关委托,替小禾和在狱中的父亲做亲子鉴定。
小禾的母亲是未婚生子,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母亲便“和别人跑了”,小禾一直与父亲、叔伯生活,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多年来连户口都没上。
孩子一天天长大,村里关于小禾的风言风语也逐渐增多,因不满儿子被说“没娘养”,父亲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一个重伤,一个入狱。
眼见到了小禾上学的年纪,父亲便在狱中请求进行一次亲子鉴定,“至少先把户口上了,这样才能让孩子入学”。
考虑到小禾一家的困难,邓亚军只收取了一半的鉴定费用,之后一个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
小禾和小禾父亲的DNA数据并不匹配,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有关小禾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邓亚军说,那是她生平第一次,极为迫切地希望自己是错的。
-

- 阜裕大桥、高铁西站、工资涨幅,这43个消息影响每位阜阳人
-
2024-12-17 20:40:4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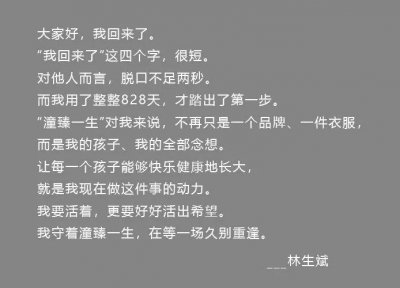
- 杭州保姆纵火案828天后,这个“死去”的男人决定好好活
-
2024-12-17 20:38:30
-

- 磨砂膏用完要洗掉吗 磨砂膏用完后多久后洗
-
2024-12-16 01:11:45
-

- 林清轩芦荟胶好用吗 林清轩芦荟胶作用
-
2024-12-16 01:09:30
-

- 张家口白河(张家口白河源头在哪里)
-
2024-12-16 01:07:15
-

- 带你深度认识熟悉而又陌生的川崎病
-
2024-12-16 01:05:00
-

- 李纯李易峰恋爱消息满天,被爆买通稿蹭热度,网友李纯是谁?
-
2024-12-16 01:02:45
-

- 童年女神拍戏时被男演员打成重伤,因后遗症含泪告别娱乐圈
-
2024-12-16 01:00:30
-

-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是几本?名字为什么叫八一农垦?
-
2024-12-16 00:58:15
-

- 赵本山的小女儿赵一涵:不靠父母的励志的富二代
-
2024-12-16 00:56:00
-

- 昆明“黑老大”死刑后复活,中央震怒下令严查,背后势力有多大?
-
2024-12-16 00:53:45
-

- 那些嫁给黑人的中国女性,后面都怎么样了?现状令人唏嘘
-
2024-12-16 00:51:30
-
- 国家承认的10家正规网贷(正规的借贷平台有哪些)
-
2024-12-15 16:41:3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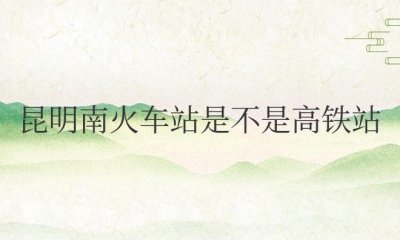
- 昆明南火车站是不是高铁站
-
2024-12-15 16:39:22
-

- 高校月饼已上线!第一个就亮了……
-
2024-12-15 16:37:07
-

- 犯太岁生肖属相有哪些? 应该怎么化解
-
2024-12-15 16:34:52
-

- 管眼鱼是什么? 深海中透明的生物还有哪些
-
2024-12-15 16:32:37
-
- 泛解单词:for的意义以及它与to的区别
-
2024-12-15 16:30:22
-

- 近现代中国的悬案有哪些 基本是凶杀案让人毛骨悚然
-
2024-12-15 16:28:07
-

- 2023年三伏天的起止时间 2023年三伏天时间表图片
-
2024-12-15 16:25:52



 广东最美警花王菲,与86名高官发生过关系,疯狂敛财上亿元!
广东最美警花王菲,与86名高官发生过关系,疯狂敛财上亿元! 亚太成员国有哪些国家
亚太成员国有哪些国家